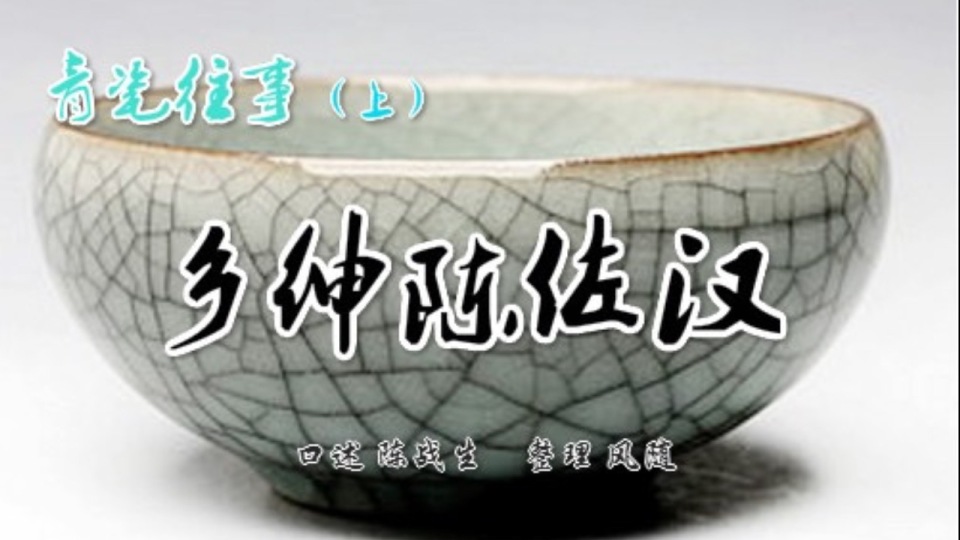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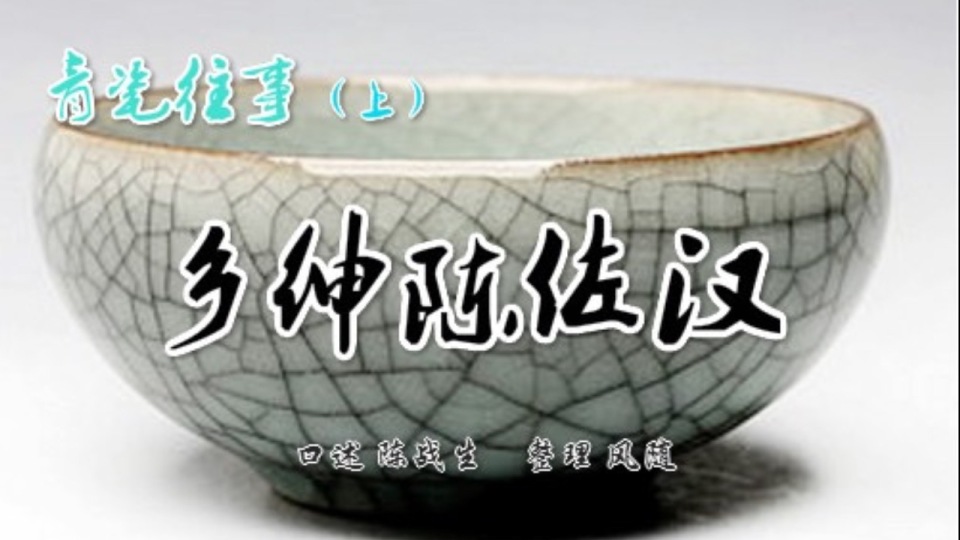
青瓷往事(上)
乡绅陈佐汉
口述 陈战生 整理 风随
浙西龙泉,盛产青瓷,产地在查田、八都、宝溪一带。
陈佐汉( 1907-1952),号六奇,浙江省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人。一生虽短暂,但经历颇丰富。他当过兵,任过两届宝溪乡乡长,做过商人,创办过造纸厂、瓷器厂,特别在传承龙泉青瓷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,为民国时期地方绅士之首举。
暑假,我回乡探亲,拜访了陈佐汉次子,85岁高龄的陈战生老人。他讲述了关于他父亲陈佐汉的往事。
父亲有空就去故宫博物院看瓷器,看到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青瓷都产自龙泉,父亲将样式画了下来,并做了详细笔记
我父亲陈佐汉,是民国乡绅社会的一个传奇,他的一生都融在青瓷故事里。
我们宝溪陈家世代以制瓷为业,在当地算是名门大户,有田地房产、有龙窑档口。我的曾祖父陈万昌开了家颇有名声的“陈万昌瓷厂”,到祖父陈有高手里,瓷厂更为鼎盛,雇佣的工人有五十多个。
1907年,我的父亲陈佐汉出生了。他是家中独子,祖父给他起名“陈范”,寓意“陈家典范”。祖父思想开明,到了父亲上学的年纪,没有把他送进旧学堂,而是送到离家几十公里外县城的“养真小学”就读。
养真小学是德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,开设有绘画、音乐、外语等科目,当时算一家开放、西式的私立学校。父亲从小成绩优秀,尤其擅长绘画。这也为他后来投身青瓷艺术打下良好基础。
父亲小学毕业后,到更远的丽水市区读初中,而后就读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,就是现在丽水中学的前身。

陈佐汉(1907-1952)
毕业后,父亲投笔从戎。一个师范生为何会从军?这要从我们陈家在浦城的族叔陈楚宾说起。
浦城隶属福建,和龙泉同处闽、浙、赣三省交界。陈楚宾在福建身处要职,北伐时期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司令部处长。1928年父亲师范毕业后,直接到陈楚宾麾下任少尉机要秘书。
1931年发生了“九一八事变”。国难当头,抗日名将朱庆澜将军组建了“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”,也叫义勇军后援会,支援东北义勇军。父亲也一腔热血,将名字改为陈佐汉,意为“佐我汉邦、驱逐倭贼”,毅然北上抗敌。

朱庆澜将军(1874-1941)
父亲先是担任“义勇军后援会”指导组事务员,后担任陆军第五十军司令部上尉军需官。开始驻扎在居庸关,后调防北京中南海居仁堂、颐和园等地。
也正是驻防北京颐和园的几年,成全了父亲的青瓷故事。龙泉青瓷几经战乱,到民国时期已衰落不堪,因技术等原因限制,八都、上垟、宝溪一带各大瓷厂出品的多是生活实用器物,就是自家在当地规模算大的“陈万昌瓷厂”,也仅仅生产些碗碟茶杯之类。艺术观赏瓷器几乎绝灭。
父亲在北京期间,有空就去故宫博物院看瓷器。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“故都壮观无不饱览”。看到故宫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青瓷都产自龙泉,父亲凭借绘画特长,将那些青瓷的样式画了下来,并做了详细笔记。

陈佐汉手稿
要不是祖母的一封书信,父亲或许还会继续军旅生涯,以父亲的学识,本是有志于干出一番事业。可他是家中独子,祖父已经过世,期间瓷厂交于他人管理,一大家子的花销颇费,生活日见窘困,祖母不得已给父亲写了信,谎称病危,盼儿速回。
父亲连夜启程回乡,行李里有一半是书籍、图册、笔记。图册即在北京驻扎期间临摹绘画的各种青瓷款式图样,也是后来出版的《古龙泉窑宝物图录》的底本。笔记则是《龙泉青瓷观录》的手稿。
回到龙泉才知被骗,但看到祖母年迈,我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生活艰辛,父亲也只能接受现实,申请退役回乡。那年他26 岁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,父亲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呈公文,为龙泉青瓷申请办理“特许专利,免税出口”,这很有超前意识
父亲振兴龙泉青瓷的想法由来已久。回来便一心投入瓷厂工作,并将瓷厂改名为“陈佐汉瓷厂”。两年后,瓷厂的生意已经有很大改观。父亲也结交了许多龙泉的名士,如青瓷名家廖献忠、书法家吴梓培等。
由于父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又有实业为本,加上有从军经历以及和隔壁浦城县陈楚宾的亲戚关系,回乡四年后也就是1936年,父亲被推举为宝溪乡副乡长。父亲当乡长还是有些便利的,很多技工怕被抓壮丁,都愿意到瓷厂来上班。
那时候父亲就意识到,想要富裕百姓,振兴地方传统瓷业是一条捷径,而且唯有依靠政府并争取政府的支持才能做好。1938年,他以副乡长身份,向县政府呈报“宝溪乡第五保溪头村碗业窑厂停闭有久缺乏资金,仰祈鉴核准予设法挽救拨款借贷建树生产”,也就是要求经费支持。父亲还自己掏钱,把一处宅院装修改建后,成立了龙泉青瓷合作社。他召集当时各瓷厂的高工师傅,组建了龙泉第一个青瓷研究所,取名“古欢室”,专门研究复古青瓷的工作。

陈佐汉雕像
当时龙泉遍地都是宝贝,造房挖土迁坟都能出土宋明时期的瓷器,父亲得到消息后总是想尽办法收购回来,他不单是为了收藏,而是拿来作研究,想还原古代的工艺。
这个研究所对我们小孩来说很是神秘,父亲带我们去过,但我们只能在大厅外玩耍,更不能进内室。“古欢室”三个字由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写,室内都是父亲的藏品,有各地出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,有名家字画,如父亲在师范学校的校友陈诚送的一幅字,还有研究古陶瓷的著名考古学家陈万里的题词。
时任龙泉县长的徐渊若,与父亲最为要好。徐是学者型县长,早年留学日本,毕业于早稻田大学,对青瓷颇有研究。父亲对徐渊若的青瓷研究工作帮助很大,徐在后面出版的几本书中都有提及。

“古陶瓷考古之父”陈万里(1892—1969)
被称作“中国古陶瓷之父”的陈万里先生几次到龙泉田野调查,得知父亲也在研究仿古青瓷,特别赠送父亲一本他写的《青瓷之调查及研究》。



陈佐汉向国民政府呈交的公文
后来父亲以龙泉宝溪乡乡长的身份,向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呈公文,为龙泉青瓷申请办理“特许专利,免税出口”,也提到了陈万里对仿古青瓷的肯定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父亲能提出“专利”的概念,还是很有超前意识的。
当时红军的随军银行就设在我们家里,楼上楼下都住着红军,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父亲唱歌,就是《国际歌》
父亲没当乡长的前两年,1934年中国红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,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,8月底红军挺进师由粟裕、刘英带领从庆元进入宝溪。宝溪的披云山更是中共西南特委的驻地,粟裕将军曾经六进披云山。
当时红军的随军银行就设在我们家里,楼上楼下都住着红军,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才知道。记得我七八岁时,跟随父亲去浦城,路上父亲唱了一首歌,我觉得很好听,父亲说是《国际歌》,跟以前住在我们家的红军学的。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父亲唱歌。

陈佐汉故居,红军随军银行旧址
那位红军就是曹景恒,他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政治部的宣传组长,因为国民党围剿,与主力部队失散,当时在龙泉、蒲城一带打游击。解放后,曹景恒当了龙泉第一任县委书记,我还和父亲一起到县委找过他。
一心想振兴龙泉青瓷的父亲,在当上乡长后,也被卷入了政治漩涡。对外他是国民党的乡长,可他又和共产党员曹景恒交好,并在我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,给游击队提供资金、药品等支援。1939年到1940年,国民党又对根据地围剿、封锁,龙浦区委被迫迁到大岙隐蔽活动,经济特别困难,父亲特意送去60元银元,还利用乡长的身份开了几张路条通行证,让游击队员黄锦华、林象春等人转移到浦城开展工作。
不久,父亲就被人告发私通共产党,被捕入狱。情况危急,我大姐,那时候她十二三岁,连夜去浦城找叔公陈楚宾报信。陈楚宾正任福建某军师团级职务,通过关系疏通,家里出了不少钱,两个月后父亲终于被释放回家。
出狱后的父亲首先做了一件事:举家迁往浦城。当时形势下,我想父亲也是考虑到家人的安危,想得到浦城叔公的庇护。之后,父亲往返于浦城和龙泉两地,既是履行乡长的职责,也是为了自己喜爱的青瓷事业。
父亲将“云鹤盘”等2件精美仿古青瓷,邮寄到外交部,作为斯大林70寿诞的献礼。第二年,父亲接到斯大林秘书的回函致谢
经过几年的研究,加上天赋,父亲对古瓷的鉴赏已具有一定的水平。且经常去上海、温州、杭州等地,与各考古名家交流研讨,对青瓷艺术越发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。
徐渊若在《哥窑与弟窑》一书里几次提到父亲。徐认为自己对青瓷研究不够,没有能力辨认瓷片,还专门请父亲帮忙,整理他收藏的青瓷瓷片,并在书中大加赞赏。对父亲在仿古瓷器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有描述:
“陈佐汉氏所仿铁骨,有时颇可混珠,若用药品去其新光,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,则好古者亦易上钩。”
“宝溪乡之溪头,有陈佐汉、李君义等,亦建两窑。原制日常用品,继仿大窑古法制器...……较诸真品,难望项背,但择其精者用弗酸浸洗,去其新光,亦可混珠,其巧者即鉴赏家亦荡然难辨。”
宝溪溪头村的仿古瓷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,在当时的市场上颇有名气,一时间京沪客商纷至沓来,龙泉青瓷又一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研制仿古青瓷,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艺术修养,从采集、辨别、分析古瓷片开始,到寻找合适的原料,如瓷土和制作釉水的紫金土,再到配方、工艺,无不需要大量时间、精力以及成本。龙窑烧瓷一窑成、一窑废,是千百年躲不过去的坎。
那段时间,父亲还撰写了《龙泉青瓷观录》和《古欢室青瓷研究浅说》两部书稿,可惜均已遗失,只留下一本《古龙泉窑宝物图录》的手稿。这部书稿,是父亲遍访龙泉、浦城各地,汇集了民间发掘收藏的100余幅古龙泉青瓷器绘图,2012年由中国书店出版。



《古龙泉青瓷文化探究》,中国书店2012年版
父亲还以各种形式和途径,扩大龙泉青瓷的知名度,争取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。1945年他收集了一批仿弟窑的瓷器“牡丹瓶”、“凤耳瓶”等,由县长徐渊若转寄中央实业部请功,一来是想得到政府更多支持,二来也是对近十年来自己包括同仁对龙泉青瓷的付出做一个总结。用他的话说:政治归于政治,实业归于实业。
其中有一件仿古青瓷特别受到蒋介石的青睐,次年获得蒋介石的亲笔赠词:陈佐汉先生 艺精陶仿 蒋中正题。
蒋介石题匾给父亲,在龙泉山城引起不小震动。但也正是这幅题匾,后来给父亲带来了灾难。

在父亲短暂的一生中,陈家窑的仿古瓷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,父亲对推广龙泉青瓷也是广开门路,不遗余力。1949年,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之机,父亲将“云鹤盘”等两件精美仿古青瓷,以“陈相刘”的别名从上海邮寄到北京,请外交部转交苏联方面,作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的献礼。
两个月后,父亲意外接到外交部转寄的信函,里面是斯大林秘书的俄文致谢:“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热爱,特许嘉奖!”当初父亲去上海邮寄,邮局工作人员还将几件瓷器当成了古董,坚决拒绝办理业务。经父亲再三解释,他们才明白,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,是我们陈家窑烧制的仿古瓷。
父亲的作品被龙泉青瓷博物馆收藏,父亲的雕像就立在青瓷小镇,父亲的故居成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。陈家的龙窑现在还伫立溪头村口,已是省文物保护单位
父亲1952年去世,享年45岁。那年,我十四岁。大哥从小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学画,几个弟弟年岁还小,算起来,我陪伴父亲的时间最长。父亲近视眼,戴黑框眼镜,在家严肃,对外人反而和蔼许多。
父亲任乡长期间,还兼任宝溪第十一民国学校校长。乡里有人叫他陈乡长,也有人叫他陈校长。父亲有空还教学生绘画。
我的母亲,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女性,早年嫁给我父亲后,父亲就去从军了。母亲一人带着我大姐和我祖母在老家生活。父亲回乡后,事务繁杂,不时有不同的人士来我们家走访,有红军,有国民党,甚至有土匪,父亲无不要应付,母亲则每天要准备好几桌饭菜。有几个穷苦学生长期免费吃住在我家,父亲在散学后还要买点日用品让他们带回去。这些事务都要母亲操持,但她并无一点怨言。
父亲去世后,我被派到浦城修水库。十六岁的我,从没做过如此高强度的工作,加上家中变故,整个人几乎崩溃。同去的一位大哥认得我,他以前在父亲的学校读书,在我家吃住过一段时间。幸好他对我照顾有加,让我体会到少许温暖。

陈佐汉次子陈战生接受采访
一天,有位穿着像干部的中年男人找到我。他是隔壁高山村的支部书记曹正方,从前是游击队员,和曹景恒一起在后方打游击。他被捕的时候,父亲受曹景恒的委托,开了个证明,说曹正方是在瓷厂工作的技工,并非游击队员,从而保下性命。其余几位战士因为无法营救,全部英勇牺牲。
曹正方拉着我的手,沉默了好久,才说了一句话:你父亲是个好人。
当时我并没思考太多人生哲学的问题,到现在我八十多岁了,再回想我父亲短暂的一生:他是个传奇,也是一个好人。

历史如大浪淘沙,对父亲的评价也云雾拨开,终得肯定。父亲的作品被龙泉青瓷博物馆收藏,父亲的雕像就立在青瓷小镇,父亲的故居成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。那口陈家的龙窑现在还伫立溪头村口,已是省文物保护单位。父亲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。
读稿人语
致敬失踪者
历史上总有一些被人遗忘的失踪者,陈佐汉可以忝列其中。这个民国乡绅不应只有“一生虽短暂,但经历颇丰富”这几字评语。如果放大了看,他一生由军而政而商而工,其传奇的复杂、细微之处,比小说家的虚构更引人入胜。
编辑 戴维
